编者按
北京时间2023年11月30日、12月1日、12月2日晚间,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欧洲科学院院士(Member of the Academia Europaea)亚当·库珀(Adam Kuper)教授走进浙江大学线上会议室,做客“海外名师大讲堂”第142场、浙大人类学系列讲座的第63~ 65讲系列活动。Adam Kuper教授是世界知名人类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理论、美国和英国的人类学历史以及南部非洲社会和文化。他也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the Huxley Medal )和里弗斯纪念奖章(the Rivers Memorial Medal)的获得者,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和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
本次活动由浙江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浙江大学人类学所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浙江大学“海外名师大讲堂”自2014年起,每年邀请海外杰出学者、文化名人、大学校长、政府和国际组织领袖以及世界著名企业高管等面向浙大师生开展讲座等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包括有近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图灵奖、普利策奖、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等来到了浙大校园。与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文化名人对话,让更多的浙大学子得以走近世界前沿领域、开拓专业视野、树立高远志向。
通过连续3场精彩讲座,Kuper教授与浙大以及国内外各所大学的师生共同反思了“人类学的若干转折时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梁永佳教授,人文高等研究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邱昱,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Jay Ke-Schutte、沈阳、Philipp Demgenski担任评议或主持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学院讲师吴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研究员薛茗与席评议。
引言
Kuper教授的讲座聚焦于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三个转折点,第一讲从马林诺夫斯基出发,讨论了他对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巨大贡献和影响;第二讲转向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从学术史的角度先后讨论了其于1948-1976年出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忧郁的热带》、《野性的思维》和《神话学》及其背后的思想转向;最后,Kuper教授以目前人类学所面临的危机,特别是人类学博物馆所面临的危机的讨论收束,围绕近年来出现在博物馆领域的几个冲击学科专业性的标志事件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
第一讲 马林诺夫斯基和人类学田野方法的革命

Kuper教授围绕马利诺夫斯基的成长、学习经历和兴趣爱好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思想渊源、贡献和问题。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出生和成长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一个波兰城市,学生时代长期浸淫在现代主义的艺术氛围之中,这种复杂的文化环境和当时现代主义运动对于“原始社会”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马林诺夫斯基后来的职业选择。从奥地利和德国毕业之后,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始了人类学的博士学习。
当时的英国伦敦,19世纪的进化人类学正在转向功能主义人类学。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主要观点是:所有的人类组织和习俗都在维系社会的层面上发挥着功能,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到这些功能。但是,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已经无法回应新的问题,功能主义所提出的问题需要人类学家长时间扎根在田野环境之中,在具体事实之中借助口头语言研究生活和习俗的每一个特点。1915年,马林诺夫斯基将这些理念付诸在Trobriands的田野工作之中,并在1922年出版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Kuper教授说,在这本书中,马林诺夫斯基向我们展示了民族志方法的魔力,由此他能够揭示出部落生活的生动图景和土著的真实观念。
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同样指出,民族志数据并不是真的在田野之中并且仅凭其本身我们就能组织它们,换言之,事实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些滥觞于他学习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8-1916)的经历中的思想,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工作的理论维度。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获取和分析数据的研究方法依赖于理论所提供的精确概念,民族志方法与功能主义理论不可分离,在功能主义看来,人类学与好的民族志并无二致。
一战前后,作为奥地利公民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澳大利亚、英国的复杂经历和身份感知,与他的田野经历发生共鸣,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中,他说,”人类学家的身份就像是一个移民“,民族志学者必须具有反身性,时刻反思自己的位置。在田野之中,马林诺夫斯基经常阅读约瑟夫·康纳德(Joseph Conrad,1857一1924,被誉为“海洋小说大师”)和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1840-1902,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左拉的作品深刻启迪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写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被体现出来:民族志中的情景描述(独木舟建造、航行)都被与一种叙述框架(库拉航行)联系起来。
至此,Kuper教授为我们梳理了马林诺夫斯基三个重要贡献(功能主义理论、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的渊源。最后,Kuper教授继续讨论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局限性,他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缺少对殖民维度的考量,但是功能主义仍然有其价值。
在讲座的对谈环节,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梁永佳教授借助Kuper教授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强调了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很容易认为理论就是抽象的理论,一种理论可以应用在新的情景中并生产出新的理论,但这是错的,我们必须了解理论产生的学术史背景。最后他与Kuper教授围绕功能主义的衰落和新的技术环境下的民族志书写展开了对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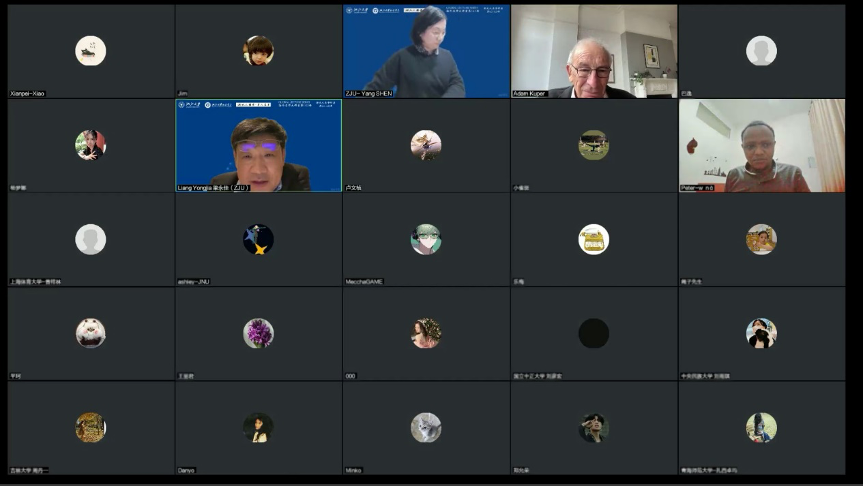
第二讲 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人类学

和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一样,通过向我们呈现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些经历,Kuper教授希望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列维-斯特劳斯在20世纪下半叶是一位如此有影响力的学者。
列维-斯特劳斯大学时期学习哲学,偏爱卢梭和康德,是一名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并对超现实主义感兴趣。他在毕业之后,1935年因缘际会成为了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因而得以在假期去巴西的原始部落中进行调查。但是,他的调查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工作迥然不同,倒更像是在旅行。Kuper教授说,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厌恶田野工作,他的田野工作只是出于对哲学的兴趣,他希望在原始社会中检验卢梭的平等社会假说,并进而产出一些新的哲学观点。
二战爆发之后,列维-斯特劳斯逃离到了纽约。在这里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社交活动之中,他遇到了一位改变他学术走向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俄国语言学家)。当时的雅各布森和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正在使用一种新的方法研究语言,寻找所有语言之中的共同结构,而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发端。在纽约的几年中,列维-斯特劳斯全心投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中阅读民族志,寻找潜藏在亲属、婚姻制度之中的基本结构。最后,他发现了“乱伦禁忌”,并认为社会通过“乱伦禁忌”构建起来,将“乱伦禁忌”与他的老师—莫斯的“礼物交换”互惠理论联系起来。1949年,《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出版,结构主义的方法开始发挥影响力。
至此,Kuper教授说,作为一个研究、阅读大量民族志材料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抛弃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观点,在巴黎与时兴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现象学家格格不入,他梦想回到新石器时代亲近自然的状态之中,他主张所有生物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人的权利。回到法国的他,为了谋生,决定写一本回忆录,这便是后来的《忧郁的热带》。“我痛恨旅行和旅行者”,这样开头的一本书之中充满了对于人口膨胀、同质化世界的悲观主义和对西方文明社会的批判。由此,列维-斯特劳斯站在了昔日的朋友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对立面,萨特说,你(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们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可是思考的方式、科学、社会都是在进步的。
作为对萨特的回应,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转向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他继承了康德的观点:“因果律并不是世界固有的,而是人们赋予这个世界的”。在此以前,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1857-1939,法国人类学家)使用“原逻辑的”形容原始人的思维,可是列维-斯特劳斯说,这种思维(图腾的、具体的、原逻辑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相较于理性的思维而言只是功能不同,没有高下之分。1962年,这些观点在《野性的思维》中被出版出来。
Kuper教授进一步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兴趣和人类学交会的另一个主题是“分类”。“分类”是民间哲学(folk philosophy)的一个关键主题,借由分类,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得以相互映射。而对于自然世界的分类在神话之中可以体现出来,全部社会的神话在想象的时间之中展开,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和动物并不是本质不同的。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四卷本《神话学》的来由,他希望借此发现人类思维之中的基本特征。
最后,Kuper教授总结到,现在,列维-斯特劳斯虽然已经不是那么时兴,但是由于“生态运动”的兴起,他的思想有可能经历第二次流行。Kuper教授说,结构主义已经产生了弥漫性的影响,成为了一种思考分类、神话系统的基本方式。
在讲座的对谈环节,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新百人计划研究员Jay Ke-Schutte围绕结构主义与语言人类学与Kuper教授展开了对谈。Jay Ke-Schutte 强调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和雅各布森的关系,以此探讨为什么列维-斯特劳斯的遗产在美国人类学传统中的接受度较低。他认为原因之一是布拉格学派在美国语言学领域的发展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在四领域人类学的背景下,由于布拉格学派的思想已经通过邻近语言学领域得到中介,因此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成为布拉格学派思想在美国人类学中传播的必要渠道。
第三讲 民族学博物馆和史前历史博物馆的危机

不同于前两讲的学术史讨论,在第三讲中,Kuper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关于人类学博物馆的最新研究(参见The Museum of Other People: From Colonial Acquisitions to Cosmopolitan Exhibitions,Profile Books 2023, Pantheon 2024)。他指出,当前博物馆面临两个危机,一个是人类学博物馆的藏品归还危机,一个是知识权威的危机,Kuper教授在本讲中侧重于后者。Kuper教授指出,当今人类学面临的危机是人类学知识权威的危机,亦即人类学家谈论其他人的权利的危机。
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涉及非裔美国人、原住民后裔、甚至意大利裔美国人等多个少数群体的身份运动(identity movement)兴起,即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种持续到现在的意识形态认为,在美国,我们必须赞美差异。Kuper教授说,这种意识形态在保存和收藏领域得到了回应。经典启蒙思想认为社会存在一个发展的阶梯,因此人类学家乐于呈现其他的社会,就是这种看法在博物馆领域造成了危机。由于一般博物馆中的原住民展览收到了来自原住民议员的投诉,1989年,美国国会决定为原住民美国人建立一个专门的博物馆,但是这样的博物馆最终被交给原住民管理,人类学家则被排除在外。在这样的博物馆的展览中,关于物品,我们只能知道物品的基本信息,无处了解它的历史,考古专家和人类学家提供的知识背景也不再存在。Kuper教授说,人类学博物馆正在陷入失去他们声称的任何权威的危机之中。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宗教自由法案》,鼓励印第安部落索取在博物馆中的神圣物品,这一法案导致了广泛的争论:被认为是神圣的物品应该被保存在博物馆之中吗?Kuper教授分享了”Zuni war gods“的案例,这些印第安人的神圣物品被归还之后,终日暴露在风吹雨淋之中,在这一事件之中,“印第安原住民的宗教权利凌驾于科学权利之上”。2020年9月,牛津的Pitt Rivers Museum撤掉了它最知名之一的展览”The shrunken heads“,新任馆长称,这项展览已经长期被当地人反对,并且对于相关人员来说过于冒犯。Kuper教授指出,这些说法并没有明显的证据,并且究竟是谁授予了相关人员权利来决定一个历史悠久的博物馆的政策呢?
在谈到这一危机的应对方案时,Kuper教授否认了将人类学收藏转移到艺术博物馆之中的措施,他认为,这种方案将导致藏品的去语境化,他说,“如果你仅把它们当作艺术品,你就是在剥离它们的本质,将它们从固有特质之中分离出来”。Kuper教授说,大英博物馆拥有超过八百万藏品,但是只有百分之一被展览过,因此博物馆应该像图书馆一样服务世界上的其他博物馆,举办巡回展览。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建立一个世界主义博物馆(cosmopolitan museum),它将超越本地、民族和国家认同,提供人类学的比较视野和专业知识,建立世界范围内的联系,为全球文化范围内的理解和团结做出贡献。
在讲座的对谈环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的研究员薛茗和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学院的讲师吴迪围绕中国的博物馆热、地缘政治中的博物馆价值、公共领域的人类学家等主题与Kuper教授展开了深入精彩的对谈。
结语
本次系列讲座,得到了校内外师生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三场线上讲座总计有超过800人次参与。广大师生就讲座内容与Kuper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本次浙江大学“海外名师大讲堂”与“浙大人类学讲座”线上活动至此圆满结束。
(图文内容|肖先沛、沈阳)